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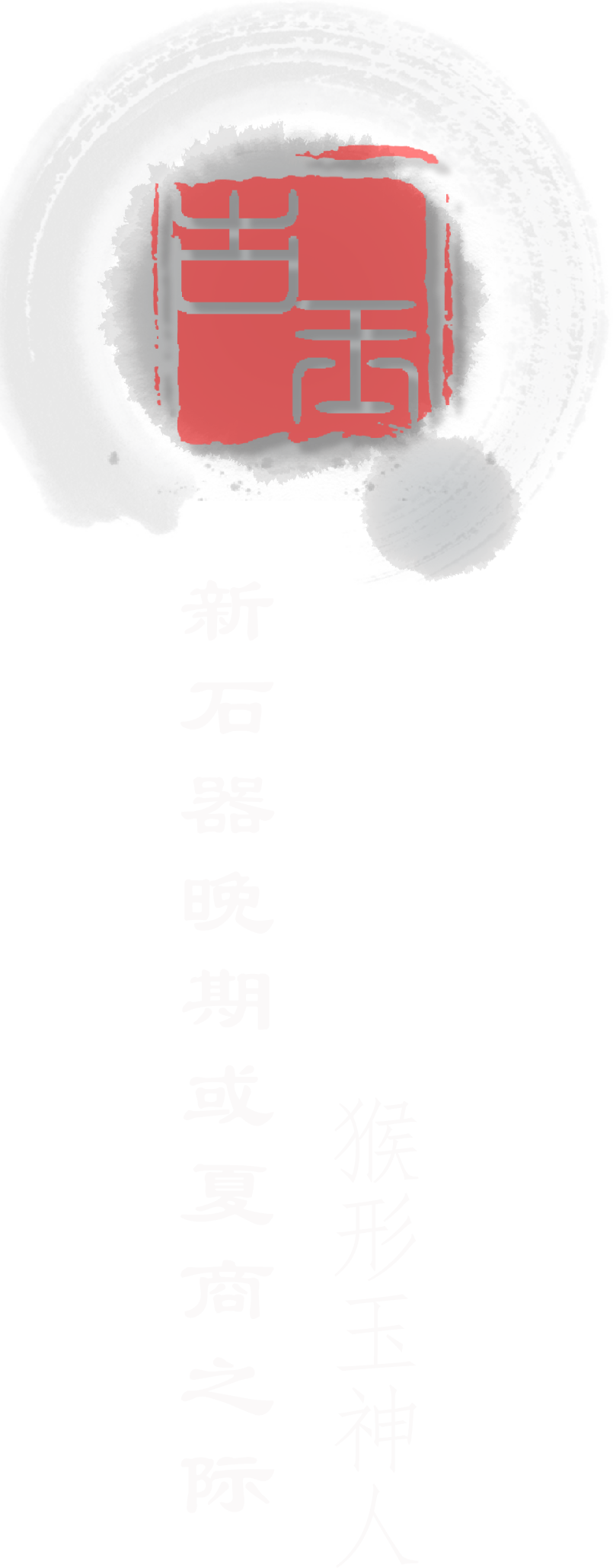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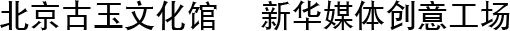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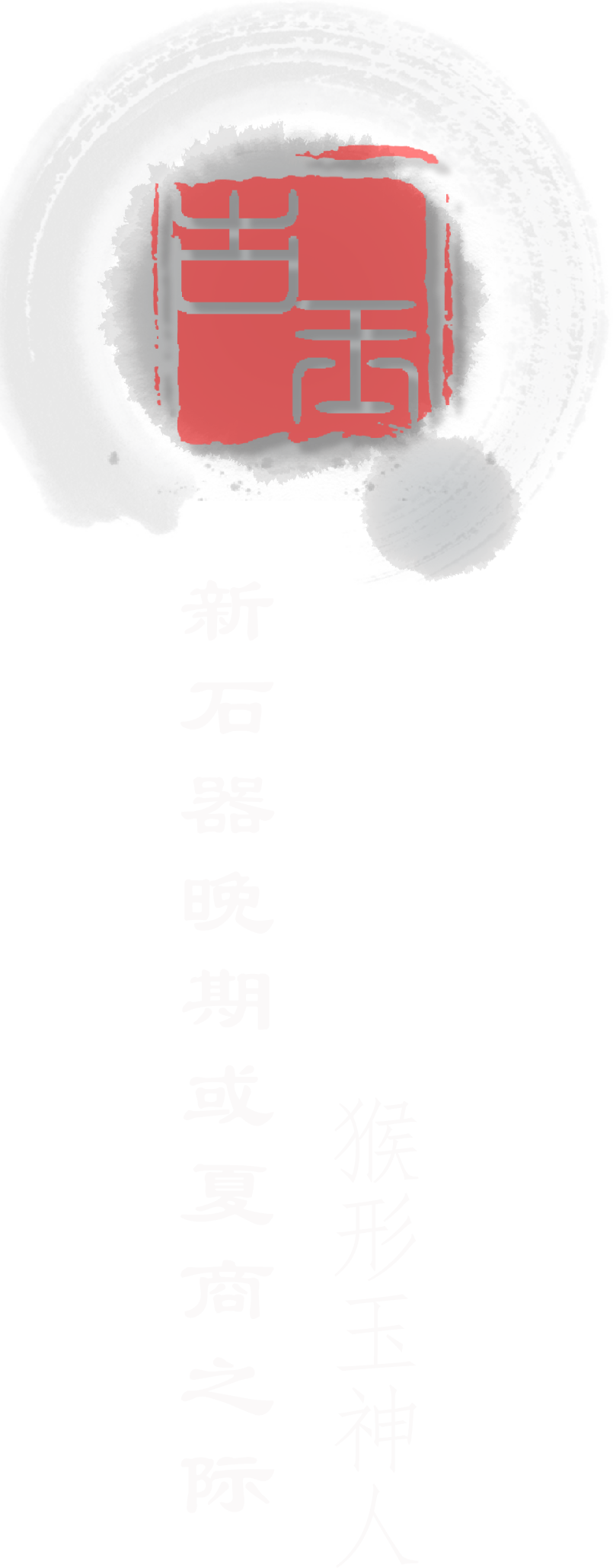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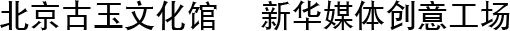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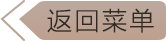


我们都知道,人和猴的渊源极其久远,人类是由类人猿演化而来。现实中,也因猴或猿形貌极肖人类、生性顽皮好动、机灵可人而深得人们喜爱。
所以,这北京古玉文化馆这尊体量巨大的猴形玉雕,就显得特别富有亲和力。它呈现我们常见的猿猴屈膝蹲坐的姿势。滚圆的双目、高扬微卷的口唇、劲健的小腿,尤其高举于上抓耳的双手,都让人忍俊不禁。
我们为什么把它断定为神人?为什么把它和神灵联系起来呢?其间深有道理。
缔造了齐家文化的齐家人,作为古羌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基本是半游牧半农耕,并且和草原文明有着很深的关系。
它们生活的区域,并不适合猴类的生存。那么,这样的猴的意念,是从哪里来的?
猴子在宗教信仰当中的地位的起源,来自古印度,而且一开始,就是和马的形象紧密相连。这在不少古印度典籍中,都有明确记载。其生活本原是因为:猴子在印度是最为多见的动物,而且,猴子还可以疗治马疾,尤其是马的皮肤病。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梨俱吠陀》、《摩柯婆罗多》、《摩柯僧袛律》中都记述说,维施努(Visnu)神的化身即为猴子或大猴,同时也是马和猿猴之类的父母。这些生活经验的积淀和宗教信仰,经过斯基泰或其他草原民族传播到了我国的新疆、宁夏和更远的鄂尔多斯草原,并把猴子与马的复合观念和猴子能给马治病的理念带到了东方。
在这里,猴子与马的组合形象,是和草原文明紧密相连。那么,这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如何传播到中国的?有两条途径。一,是斯基泰或其他草原民族,把它传播到中国北方草原文明所覆盖的地区,并逐渐延伸;二,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新疆,再继续传入内地。
就后者,鄂尔多斯出土有大量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系统特色的青铜短剑、环首或兽首刀、动物牌饰,与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什克出土的同类文物造型风格基本一致。其所属文化为塔加尔考古学文化,且两者的时间基本相同。这说明双方的文化之间有相互往来;并且,鄂尔多斯是受塔加尔文化的影响。两地都出土猴子骑马的青铜饰件,可能就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就后者,上世纪二十年代,西方考古学家西方人赫定在新疆和田约特干也采集到一件猴子骑马的陶俑,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中国河西走廊地区,还有更多这样的考古发现。上世纪 90 年代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出土了“胡商牵驼模印砖”,上面就有猴马组合;新疆高昌故址出土有南北朝时期对猴团花剪纸,唐代更有猴子骑骆驼陶俑被发掘出现。
作为齐家文化典型代表的这件猴形神人,我们认为,它和上述内容中的前者,关系比较密切。更和古印度文化中的维施努(Visnu)神的化身即为猴子或大猴关系至为密切,因为他们都关涉远古人类的神灵崇拜。
也许,在我们梳理的这两条古印度文化传播路径之外,还有着更加久远的东西方交融玉碰撞,更需要我们去关注和思考。